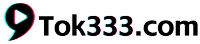责任编辑: bmorevapes.com
不知从几时开始,伦敦街边的连锁快餐店开始投放“素食汉堡”,以炸鸡为招牌的几家快餐店也推出了“无鸡肉汉堡”。进餐馆吃饭,不论餐馆级别高低、规模大小,在主菜单之外都会附有一份素食(vegetarian)或纯素食(vegan)菜单。身边一对坚持纯素食多年的姐妹在闲聊时提起来,从前下馆子都要事先打听餐厅是不是“善待素食者”,或者到餐厅点菜自称“纯素食”时,心中总不免忐忑,随时准备他人投来奇怪的打量。可是今天她们觉得这种异样感已经在不知不觉间消散。
英国今日已是全欧洲植物奶制品和植物肉类的最有力消费者。根据The Vegan Society的调查显示,今日英国餐厅内有四分之一的晚餐是素食,跟以往相比,每三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减少了对肉类的依赖。而据调查网站Statista今年三月底的数据显示,全英国素食者和偶尔吃鱼的素食者一共占比7%。素食趋势在年轻人群里尤其突出,20岁以下的英国成人当中,素食者已占11%。根据英国美食外卖平台“户户送”(Deliveroo)提供的数据,过去一年里消费者对素食餐品的外卖需求量激增117%。
伦敦的各家连锁和独立咖啡门店里,如今都会引入替代牛奶的植物奶,以备不时之需。在植物奶制品中,豆奶、燕麦奶最受欢迎。燕麦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一位瑞典科学家的研发成果,而豆奶则是中国人很早就熟悉的日常饮品,从东汉时期就已有记录,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成为时尚饮品。但今日英伦咖啡馆里的新潮物种、纯素食者引以为傲的牛奶替代品“soy milk”,却是在20世纪下半叶才被欧美人认知并逐渐成为抢手风潮。“破壁机”磨鲜豆浆早已在国内普及,我在伦敦偶尔跟朋友提起来,却被视为酷得不得了的新事物。
伦敦的素食餐厅也随之越开越多。提起“素食馆”,在广州成长的我马上联想到的是寺庙里外的“斋菜馆”,当然还有一般餐厅中一道名为“罗汉斋”的蔬食杂烩。其实国内多个菜系里,不带肉类的菜式多的是,只是没人专门去挂上“素食”的标签而已。南北方的家常菜里,任凭谁都能随口就说出一堆来:豆角烧茄子、地三鲜、椒丝腐乳通心菜,以及带“清炒”的各种蔬菜,等等。
而英国人传统爱吃大肉,蔬菜一向只是“配菜”(side dish)命。过去数年间我与多位英国厨师闲聊或做采访,都会随口问起他们心目中的英格兰经典菜,出现频率最多的是Sunday roast(礼拜天烤肉)。这个延续至今的传统源自亨利七世时代,国王的卫士每周日在教堂做完礼拜后会去吃一顿烤牛肉午餐。17世纪时的英格兰人甚至一度有个“beefeater”的绰号,大家也引以为傲。那个时代英格兰曾流传过一首名叫“The Roast Beef of Old England”的爱国歌曲,时至今日英国海军坐下就餐时,还保留着哼唱这段《老英格兰的烤牛肉》之歌的传统。
从早期罗马、维京人入侵,到近代扩展各国殖民地的过程中融入进来的各种影响,英国人的餐桌传统发展到当代,不变的主题是肉类和根茎蔬菜。英格兰第一个提倡素食的组织虽在19世纪中期已出现,甚至随后不久就迎来第一家素食餐厅的开张,但素食对大众真正产生深远影响,还要等到20世纪末。一般英国家常菜或英国菜的馆子里,典型的一顿饭是以鱼或肉为主菜,配少量蔬菜和土豆。然而过去五年间下馆子时,我发现了明显的变化。比如从前在英国餐桌上不起眼的花椰菜,摇身变为能取代牛排位置的主菜:一道烤横切花椰菜,已成为今天多少餐厅素食菜单中的顶梁柱。
根据国际素食餐厅查找平台HappyCow在2019年显示的数据,伦敦是当今世界上180个国家和地区之中对素食者“最友好”的城市,疫情前已拥有超过150家纯素食餐馆。疫情解封后,纯素食馆的热度有增无减。今年初,伦敦的百年百货公司Selfridges里也请进了一家由美国名厨Matthew Kenney开的素食餐馆Adesse。到这家新餐厅里坐下以后,我想起了前段时间认识的一位澳大利亚姑娘Dom Hammond。原来是电影人的她五年前移居印尼巴厘岛,慢慢探索当地的热带蔬果、采摘海边野生的仙人掌,自己研究仙人掌食谱,逐渐成为专事蔬食烹饪的厨师。我记得Dom跟我提到过她不喜欢市面上流行的用蛋白制品制作“素肉”,她用做料理的食材全部用蔬菜水果组成。
我也不喜欢蛋白质品模仿的“素肉”,这也是自己向来对素食餐厅抱有保留态度的一个原因。半带犹疑地在Adesse吃完一顿饭,吃着吃着就发现,这样一家馆子未必只吸引纯素食者:用开心果、向日葵籽磨浆代替传统奶酪、用豆奶打成“奶油”、汉堡里用野菌杂烩代替牛肉饼的做法,就令我这个非奶酪爱好者的非素食人士有如沐春风之感。而用节瓜、土豆、鹰嘴豆做汤;用土豆丝、块根芹切丝、苹果茴香分别切丝拌成沙拉;用橙子肉配上麻油炒甘蓝菜等等菜式,更是令“纯素食”这张向来让人联想“节欲”的冷面孔变得十分亲切。
文章编辑: bmorevapes.com